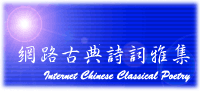梅弟:
我上站上得晚,人家園子門上了鎖,進不去,您囑咐要我說的話便說不得了,祇能在此抱個歉。
二姊我別無高見,但知詩之為詩,就是同「常言」有異。既非常言,則變古弄怪、炫奇出新,自是當行本色。不能懂,偏是詩,自不必假一義而縛之、持一器而膠之,此之謂「天倪」。一看就透天明白的反而不好意思說是詩了。所以,詩不弄玄虛,教誰來弄玄虛呢?詩當然要弄玄虛,祇是不止於弄玄虛一途而已──然則,也可以說是弄者與不弄者各持一端、互相不許而已。
來一首舊作惹笑:
聲聞緣覺果如何,密學雕蟲事苦哦。斲落常言爭囈夢,嘶酸肺腑看誰多。